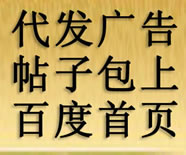“看了視頻后再看警情通報,二者之間存在很大的差別與不符。”
原本自以為9分57秒鐵證在手,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發布了一封義正言辭的公告,沒曾想卻因“錄上了嗎”四個字將自己置身于人民群眾的口水中鞭撻,丹東方面的這一番操作,不得不說,確實是“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”。

事情的經過已經傳播得非常詳細,到底誰對誰錯這種沒有統一認知的無效討論就不再贅述,直接上干貨。
確鑿可查的第三視角影像顯示,70歲的丹東郝大爺護女心切,情急之中扇向丹東民警的一巴掌并沒有碰到他,而年輕的民警卻在沒有被郝大爺打到的情況下順勢倒地,還忙不迭的回頭問同伴“錄上了嗎”,這個細節足以證實,丹東民警涉嫌“碰瓷”,有“釣魚執法”之嫌。
如果僅憑“碰瓷”方式錄下的影像,就給一名70歲的老人定一個“襲警罪”,將置法律尊嚴于何地?置公平正義于何地?置執法為民理念于何地?
面對輿論的沸騰,丹東方面不能關閉評論了之,必須給公眾一個交代。就像網友所說,“就單憑倒地撒潑打滾這一出,警服警徽你穿戴的也不合身。”
這里面最核心的問題就是,郝大爺扇出去的一巴掌,到底算不算“襲警”,哪怕是成功被錄像取證了,是不是“襲警罪”就沒得跑了?是不是碰一下民警就觸犯了“襲警罪”?
“襲警”二字僅憑字面感觀就讓人覺得非常嚴肅非常嚴厲,既然能冠之以“罪”名,顯然在罪責認定上也不能草率行事,必須慎之又慎。“襲警罪”不是“霸王條款”,定罪與否也不是簡單一段錄像就可以判定的。
眾所周知,大陸法系國家中并不存在單獨“襲警罪”,而我們的“襲警罪”也僅于2021年3月1日起,才在刑法“妨害公務罪”中予以明確,“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的,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;使用槍支、管制刀具,或者以駕駛機動車撞擊等手段,嚴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,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”。

對于什么是“暴力襲擊”,《關于依法懲治襲警違法犯罪行為的指導意見》中也有明確定義,比如,“實施撕咬、踢打、抱摔、投擲等”,“實施打砸、毀壞、搶奪民警正在使用的警用車輛、警械等警用裝備”,“未實施暴力襲擊,但以實施暴力相威脅”。
誠然如四川大學法學教授韓旭所言,丹東一事的起因,源于郝女士被民警拖拽倒地,情急之下作為父親不可能無動于衷,郝大爺僅僅是上去打了民警一巴掌,性質并不嚴重,情節并不惡劣,完全可以依照我國《刑法》“但書”的規定:“情節顯著輕微,危害不大,不認為是犯罪”來處理。
韓旭教授稱,雖然《刑法》修正案增加了“襲警罪”規定,意在對警察執法給予特殊保護,但必須注意個人權利與警察執法公權力之間的平衡,不能將法律的天平過分傾斜于警察,也要考慮行為的起因、性質、情節和后果等,不能僅僅有撕扯行為或者打了警察一拳就對行為人以犯罪處理。
舉個例子來說,如果你認為民警執法不規范,或者執法不公,進而當面提出批評意見引發爭辯,就算爭辯到非常激烈的程度,也不能隨便以襲警罪追究;再比如,你對民警執法進行拍照,被沒收了手機,一時情緒激動雙方發生撕扯,對執行職務的民警實施了輕微暴力抗拒,也不能以襲警罪論處。
具體到丹東郝大爺的扇空了的一巴掌,在壓根沒有接觸到民警身體的情況下,顯然不符合“襲警罪”構成要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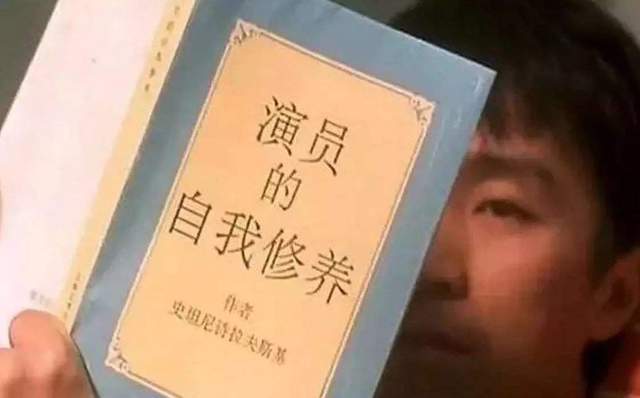
襲警罪施行首日的2021年3月1日,發生在江西萬安的一個案例顯示,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強制傳喚的袁某被帶到警車后,“用雙腳踹壞后車窗玻璃,在民警對其控制期間又多次用腳踹兩位民警,并在途中言語威脅、恐嚇執法民警”,“到派出所后,抗拒審訊,腳踹訊問民警”,“經鑒定,致兩位民警人體損傷程度達到輕微傷”。據此,袁某因“犯襲警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個月”。
韓旭教授認為“入罪應遵循刑法謙抑精神”,丹東郝大爺扇向民警的一巴掌,雖然民警機敏地倒地極大提升了一巴掌的視覺沖擊力,但遠未達到襲警罪所必須的“暴力襲擊”程度,丹東公告宣稱的“涉嫌襲警罪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”明顯失當。
襲警罪的明確是“為切實維護國家法律尊嚴,維護民警執法權威,保障民警人身安全,依法懲治襲警違法犯罪行為”,絕不是可以隨意定性的“霸王條款”。肆意擴大襲警罪定義范疇,反而容易引發法學界擔憂的“產生不適當地擴大刑法打擊面,破壞刑法分則現有的合理結構,產生新的罪刑失衡問題等弊端”出現。
“釣魚執法”并不罕見,但千萬別讓“碰瓷”定罪這樣的惡行浸染于基層公安系統,這種壞頭一開,后果不堪設想。
好在,丹東方面“已注意到網絡輿情”,并表態“正在進一步調查”,期望他們盡快給公眾一個交代。

千萬別讓“影帝”、”碰瓷“、“弱不禁風”成為民警洗脫不掉的標簽,稀釋公信力,這種傷害,顯然遠超郝大爺打空的一巴掌。